离开电导除了最后一段经历对陈沓来说比较离奇以外,别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正换个公司对陈沓来说即不是第一次也将不是最后一次。陈沓觉得可笑的是他的加拿大同胞老喜欢把鸡毛当令箭,在夫妻店里演军事演习,一百来号人的小单位里值得凭什么跟同事下绊子、使小心眼、犯自由主义、耍两面派吗?
不过离开电导让陈沓婉惜的确实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能再跟程序员Alex Volnov聊天了。在认识Alex Volnov以前陈沓对苏联老大哥没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在研究生院里见到的老大哥,要么是英语学得不好,要么是家教学得不好,除了用祈使句、反问句、设问句以外,好像不太会用陈述句。认识Alex Volnov以后陈沓才相信“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但是在适当的场所底下也不相信盛气凌人。Alex好酒如命,这不是什么好的值得学的地方,不过别的方面就不错,比如不怎么好色,一个老婆一个孩子,跟陈沓一样. 年纪跟陈沓一样大,个头比陈沓高得多,说到计算机比陈沓懂得多得多,尤其是谦虚的态度和对知识毫无保留的态度让同事们个个受益,人人赞扬。陈沓总结Alex对待同事的态度是:我教了你知识并不会使我的知识少啊,我教了你两下子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能学到新的两下子。于是Alex不断地给同事们传经送宝,但仍然是最高明的程序员,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
不过陈沓和Alex最喜欢谈的话题并不是电脑或者编程序,而是关于语言和人的名字。哥俩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说起的,Alex的家乡是来自黑海之滨的Krasnodar,他解释说这座城市原名叫Yekaterinodar,其意义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给的礼物,后来革命了就改成了Krasnodar,其意思是红军给的礼物。陈沓告诉Alex Volnov:我的家乡叫“贵阳”,官方的解释是“贵山之阳”的意思,但是许多中国的老百姓都把它解释为“太阳很金贵”的意思,因为那座城市附近的地区素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著称。可是咱们的同事桂兄弟,把贵阳解释为“重男轻女”的意思,说“只贵阳,不贵阴”,看来他们台湾人学的中国文化就是有问题。不管怎么说吧,我每次用英语给别人说我的家乡叫“Gui Yang”,我总是觉得心里挺难受的,这“Gui Yang”有什么意思?把这家乡的名字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位Volnov老大哥告诉陈沓他也深有同感,他的姓“Volnov”在俄文里面是“波浪”的意思,他觉得说在英语里边也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味同嚼蜡,他很希望到电话本里去把自己的名字列成Alex Wave。陈沓说:“哟,你的名字跟那个叫张涛的程序员,志向是一样的,你们的名字里都有‘兴风作浪'的成份。而且你们有雄心壮志的话,就大开大合,掀起惊涛骇浪。”
接下来陈沓和Alex都觉得,这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名字在翻译中都丢失了美感,太可惜了!尤其是许多名字在翻译中还产生了错误,多么影响文化交流啊!俄文里边把中国叫做Китай,追溯起来就是契丹的意思,中国等同于契丹?! 那《天龙八部》里的萧峰不就不可能是叛徒了?那还有什么故事情节啊?
“Bull,是公牛的意思。Lock是锁的意思,Bull Lock放在一起就是公牛锁的意思。”像Sandra Bullock如果翻译成桑德拉布罗克,怎么能比得上桑德拉公牛锁这样的艺名更能体现他的银幕形象呢?还有Nicolas Cage,Nicolas是人民必胜的意思,Cage 是笼子的意思,像尼古拉斯凯奇这样的翻译,怎么能比得上“人民必胜,铁笼子里面待着去吧”这样的翻译更有意思呢?
陈沓接着列举,我以前有个老板叫Jackson,Jack是千斤顶的意思,Son是谁的儿子的意思,像他就是如果翻译成“千斤顶的儿子”,能显示出他不屈不挠契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如果把他翻译成杰克逊,那就太一般了;像Bill Gates这样的名字,Bill是帐单的意思,Gates是大门的意思,把两个词放在一起,那就是帐单派的掌门人?如果你说Richest person on Earth, Bill Gates,你可以翻译成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但是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帐单派掌门人钱老大;像Martin Luther King吧,中文翻译成马丁路德金,King就是国王的意思,那跟中国姓王的,是一个意思,所以这马丁路德金,是老王家的骄傲啊。老王家这孩子王马丁,后来做了洋博士,中文叫王博,英文叫Dr. King,领导美国黑人抗暴争民权,当时毛主席发动中国人民唱着歌给他加油啊:“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如今美国人民为了纪念王博士也一年放一天假,王家那么重要的一件大事怎么能在翻译中弄丢了呢?
后来Alex和陈沓老在他们认识的人中积极地开展“正名运动”,引得有的人积极参与,有的人哭笑不得。陈沓心想,现在我离开了电导,Alex只好去跟J.P一块“正名”咯。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眼前还是饭碗要紧啊。
在领了一个月的下岗补助以后,陈沓在本地的大专院校里找到了一份教书的职位,脱离了失业大军的陈沓,开始半天做上辛勤的园丁,另外半天积极发展第二产业。
在陈沓心中,关于创业和谋生的技能训练,大部分是从.com的肥皂泡和千年虫的铺张浪费时代耳濡目染而学来的。那是一个接近二000年左右光怪陆离的年代。在北美各大城市,总是有人从加利福利亚、硅谷之类的地方学来了宝贵的大寨经验,于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试验推广。找他一片旧厂房、旧仓库、老工业区,把它们变成办公区,于是一大堆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公司开始挂牌营业,这种靠风险投资公司的资本烧出来的一片高技术产业区往往被人叫做高技术培养皿地段。在这样的地段里,阿Q们做着“喜欢谁就是谁”的梦,干着“要什么就拿什么”的事。风险投资大家花起来都不心疼。于是一大堆败家子,吸引来了别的许多服务产业,比如服装业、餐饮业。一片过去死气沉沉的工业区俨然显出一幅如火如荼的革命景象,奏出一曲革命高潮的大浪掏沙的凯歌:“嘿……大江东去浪淘沙,革命的洪流冲天下,砸碎镣铐和锁链,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歌词里边接着说下去是: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工农政权扎下万年根。
人跟人哪儿那么容易团结一条心啊,从一九二五年的攻克武昌,到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高潮总是这样,就像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快。二000年左右,英特网和股票市场也就折腾那么两三年吧,一直持续到二00一年的9.11,这段被人称作.com的时代,才彻底像吹涨了的气球一样“噗呲……”被人戳了个洞。
陈沓回忆起在高新技术培养皿地段生活的日子,大伙儿不管是换工作还是找生意,经常是在同一个行业里窜来窜去,尤其是搞市场销售和推销的人,经常这么干。这家公司倒闭了,那家公司开张了;今天是保皇派,明天是支红派;今天为同志们干活,明天为敌人干活;今天做老北京的旧警察,明天做人民的新警察;今天批林批孔批邓,明天深揭狠批四人帮。抱不住一个铁饭碗抱他一百个一次性的纸饭碗,干净、卫生、清白。竞争对手嘛,不打不相识。三十到五十年以后竞争对手们聚在一起对酒当歌感叹人生几何,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时候才发现,职业化商业化并不是人类进步以后才有,其实自古有之。从孔圣人周游列国,苏秦张仪连横合纵,到孟尝君狡兔三窟,还有洋人哥伦布到处求赞助航海,到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边在英国求官,一边在美国闹独立,只要不是太缺德,大家都称他们为职业队员。人品不太好的,像吕布、甫志高、王连举或者Benedict Arnold,大家就把他们称为叛徒。陈沓想做个叛徒,但是又不想跟法律准则和社会公德太过不去,于是他想起一个做市场和销售的英国同事Eric Cutler取经。
既然Cutler先生的名字中有cut,也就是“砍”的成分,那且把这位先生叫做“砍大山”老兄吧。当陈沓联系上“侃大山”老兄并把自己被炒鱿鱼的情况给他简短说明了一下以后,“侃大山”老兄爽朗的笑了说:“哈哈……看来安卡真是照准你的裤裆狠狠地给了一脚是吧?”陈沓说:“是啊。贾药师傅在我背后还捅了一刀,他们让我难受,我也让他们自在不了。哎我说老兄啊,你不是搞市场的吗?你看这个电导的行业里,他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啊?你应该有一份名单吧?”侃大山老兄很快的在电子邮件上给陈沓送过来一张名单,在挂电话以前侃大山老兄改变了吊儿郎当的语气,然后说:“David,我跟你说两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冤冤相报何时了,以眼还眼,全世界都会瞎了眼,这是圣雄甘地说的。”“我不知道像安卡这样的人信不信地狱,但是他们印度人多半相信转世,让他来世变只蜗牛好了。你何必在今生跟他过不去呢,你一定要在电子导航这样的行业里工作吗?何必呢……”
陈沓谢过侃大山老兄挂了电话以后开始思前想后,侃大山老兄也是前电导的雇员,也是在安卡过河拆桥以后掉到河里去的,不过安卡对侃大山老兄过河拆桥以前,是因为对另一个伊朗的女博士Doctor Shababi(中文翻译成“流星博士”)过了她的河然后拆了她的桥,流星博士在英国的法院上控告了安卡,侃大山老兄是电导在英国的剑桥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有正义感,敢于挺身而出支持流星博士的控告的雇员,他的旁证最终使电导在英国赢得了一个恶劣雇主的裁决,所以当安卡对侃大山老兄过河拆桥的时候,不仅是过了他的河,而且还跟他结了梁子,一定得拆他的桥。
陈沓跟侃大山老兄有过一次冲突,那是在“北方之星”项目的中期,有一辆“北方之星”的出租车装了电导的报警系统,有一天车里载了一个喝醉了酒要闹事的醉汉,驾车的的哥暗暗地扯了两下报警系统以后,没见着反应,这位身高一米九五平常爱好体育的的哥活动活动关节以后把那醉汉扯下车来胖揍了一顿。然后悠闲的用手机把警察、救护车和同事都叫来了。电导的系统出了故障,陈沓和同事们本来手里都捏了一把冷汗,幸好“北方之星”的的哥武艺高强,没出什么大岔子。
第二天早上,陈沓和另一位在“北方之星”的修车厂里当班的电导技术员收到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电子邮件,这份电子邮件把本来严肃的技术故障推进了马戏团和娱乐圈。邮件的作者是Olof同志,一位“北方之星”专门雇来与电导交涉的党代表。Olof 抛弃了自己平时写英语时一幅欧洲人的文 绉绉 的文风,留下了以下亲切的话语:“昨天,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发生了一场妈拉疤子的真格儿的斗殴,一个醉汉乘客毫无原因的用自己的头不断地撞后车门,然后又不断地用头撞车的前车盖儿,撞出了好几个明显的大坑儿。最后这位乘客不顾我们司机同志友善而耐心地劝阻,用他那暴力的头狠狠的撞向了车的前窗,砸碎了车的前窗玻璃,直到警察同志来到现场,才把这个进攻性极强的乘客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我们的司机同志才脱离了生命受威胁的处境,得到了人身安全。”
跟陈沓在一起的英国技术员名字叫伯纳,可是不姓萧。伯纳在收到了Olof的电子邮件以后批注了一句“Olof一向强调司机的安全,可是乘客的安全到哪儿去了!!!”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然后把这封电子邮件以及他的评语传给了电导的许多同事,电导的许多同事都起哄说“好玩,真好玩。”只有侃大山老兄对陈沓说“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低头认罪,没什么好玩的。”陈沓和伯纳都被冲得难受,嘟嘟啷啷的说“我们只是笑那电子邮件的内容,并没有笑整个故障。”不过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强词夺理。
当时还没怎么印象特别深,但时间久了以后陈沓越来越觉得,侃大山老兄确实理高一筹,尤其是与许多做市场和销售的同事比起来,陈沓觉得侃大山老兄的道德标准也太高了点,这不要出污泥而不染吗?我真向侃大山老兄看齐吗?陈沓问自己: 我真能忘掉一切该忘掉的事, 然后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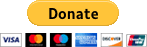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