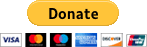| 中文 | 收听|Listen | English |
|
离家出门,有一位爱说怪话的幽默作家写到过:"I tried to run away from home,ever since I learned how to walk。"
一推门,开门见山,在贵阳是这样,温哥华也是这样。打个的,穿过大街,走过人群,那位被印第安人叫做摇杆红缨枪、中国人翻译为莎士比亚、英文名字叫"Shakespeare"的老作家曾经写过:"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这种舞台和演员的荧幕效果,走进车站、机场更为明显。每个男女在一生中该演的七个角色,像春晚小品一样出现在眼前,婴幼儿、学生、恋人、士兵、法官、绅士,最后又返老还童,掉了牙齿,眼前模糊,失去味觉,失去一切,要不人家怎么被尊称为"莎翁"呢?伟大的剧本就是要上演千百年。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火车站那个乱哪,悲情啊!
哦哦. . .
曾经以为我的家
是一张张的票根. . .
过几年大家都改坐飞机了,觉得飞机场宽敞明亮。再过几年全球化了,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现代人牛啊,掀起了把世界上的飞机场变成火车站的运动。以前听着响当当的虹桥机场被中国人变成了火车站,希思罗机场被欧洲人干成了火车站,温哥华机场正在朝此方向努力. . .
混乱的机场使人眼花缭乱,不知道有没有使人精神病发作。精神病有关的单词在日常生活中用得不多,比较难记,属于GRE词汇。可若是星期一早上,进了温哥华机场,去赶美国航班,这样的词汇直往耳朵和脑子里面蹦,paranoia、hysteria、delusional、schizophrenia。
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陈沓还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 . ."那狂人哥们可能得的就是schezophrenia,语言错杂,无伦次,荒唐,还狂想。那位叫Alfred Hitchcock的导演,是否也喜欢schezophrenia?他眼瞅着Ingrid Bergman,深情地望着爱德华大夫,爱慕的眼神轻轻地呼唤着亨利·亚当,旁边赵家的狗以奇怪的眼神看着大家,心里嘀咕:怎么那么多老外呀?
"下一个!"陈沓听见边防官员叫自己,乖乖地把护照和填好的表格递过去。本想着拿了加拿大公民以后进出美国会比较容易,可是容易了一两次以后,又开始不断地被这些边防官员送入"研究研究谈话室"。
这片"研究研究谈话室"面积还蛮大,有一个柜台,后面站着边防官员,柜台的另一面,是那些被仔细端详、仔细审查的想去美国的乘客们。既然是仔细审查,乘客们就被一个一个、一家一家的叫过来,没叫到的在远一点的地方,一套玻璃门窗外面稀稀散散地坐着,听候传呼。
但是边防人员们都是一帮不把老外放在眼里的老外,所以不急着把老外叫过来审查,有空的时候在服务台后面可以聊聊天呀,看见一刚休假回来的同事就问:"Hello,Stranger,how is your vacation?"
"Oh,too short,I’d rather be at the beach。"
一提到海滩,男的女的都凑过来聊天。
我爱金色的阳光
我爱蔚蓝的海洋
我爱自由的漂荡
我爱白云的故乡
. . .
后面等着过关的老外这个急呀,可是没办法。
飞翔,飞翔,我爱飞翔
飞翔,飞翔,我爱飞翔
这帮边防的哥们儿姐们儿接着"阳光-阳光-阳光-阳光,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 ."聊得尽兴了,全部说完了,看看电脑屏幕上下一个名字是什么,然后叫进来审查审查。
"Da Chen!"是老外传呼陈沓时的发音,陈沓来到柜台前,看见将要审问他的这位官员,在该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地方佩戴着一个小铁牌,上写"Curretz"。
若是以印象派的手法作画,看见一个物体像什么,就把它画作什么;若是以印象派的手法作文,看见一个人像什么,就把他说成是什么,比如鲁迅说"细脚伶仃的圆规"。这位名字发音以"柯"开头的边防哨所官员可以用印象派的手法描述成是一个大大的核桃,放在一个更大的啤酒桶上。
他垮着脸,间隔一断时间,眼珠子像探照灯一样左右慢慢扫描一下,约一百三十五度范围,时不时地瞪着屋里的人或者物体。在有着空调和暖气的屋子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千万不要忘记反恐斗争。
当他的眼珠子停下来以后,瞪着陈沓,声音里带着铅块说:"你要去哪儿?"
"我今天要去休斯顿。"
"你去休斯顿做什么?"
"我最近的工作是在休斯顿做一个项目。"
当这位"柯"边防听到陈沓的回答里面有"工作"两个字以后,立刻显露出了他的大名,翻译为中文应该是什么,跟《笑傲江湖》里面的岳不群、陈不忧、封不平一辈,这位"柯"边防的大名叫"柯不爽",江湖上人称"软硬核桃"。
"你是说你要到美国去工作?你有劳工认证书吗?"
陈沓说:"没有,我的雇主不在美国,我也不会在美国长期工作,我两个星期回加拿大一次。"
柯不爽更加不爽,说道:"你以为我的智商是可以低估的吗?Are you try to insult my intelligence?"这是一句挺能上得了场面的话。柯不爽说出这句话觉得不容易,左右看看有没有哪位同事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而对他刮目相看。
"Ha-Ha,I just want to call you a girl。"陈沓望着核桃表面一吊一吊的太监脸上一般的肉,和一个胖大妈的黄桶腰,很想这么说,但是如果那么说了,自己的前程就断送了。有水平的领导都会说:"我现在不说,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说。"于是陈沓什么都没说,玩了一个"沉默是金"。
核桃没能从同事们当中找到欣赏的眼光,失望地对陈沓说:"等着。"然后拿着陈沓的护照和文件,进了几间比较隐蔽的办公室,做起了他的serious detective work。detective,一个形容词,也可以作名词,作名词的时候可以翻译为"侦探",比如像福尔摩斯。美国一般老百姓喜欢把穿着制服的警察叫做Officer,级别高一点的便衣警察叫做detective。
陈沓记得在美国刚买房子的时候,街坊邻居里面老中并不多,有一些调皮而讨厌的邻居的小孩想给他来个恶作剧,恶心恶心他,最好能把他赶出国门之外。
有一天陈沓回家发觉留言机上留了那么一段话:"Hi,this is Detective Lansky from INS,we found you being an undocumented illegal immigrant,and you also part of the Korean gang,we are going to come your house at 3’clock tomorrow afternoon,Ha-Ha. . .I was like. . ."
于是陈沓找了一个穿制服的Officer来家里听了这段录音,那位Officer跟陈沓说:"移民局的官员没有Detective这个头衔。"移民局,也就是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简称INS,里面的官员一般被人称为Agent。所以若真是移民局官员留的言,应该说Agent Lansky,而不应该说Detective Lansky。他叫陈沓放宽心,从留言者分不清楚Officer、Detective和Agent这三个单词的用法上看,留言者多半是一个白痴--An idiot,不足为虑。
上了那么一课高级英语,一下了解了那么多单词的细微差别,陈沓心里轻松了许多,真正体会到了知识就是力量。那位Officer还安慰说,他第二天下午三点会在附近巡逻,使陈沓觉得美国派出所一级的警察同志们还是跟移民很友好的。
在机场的"研究研究谈话室"里,这些穿制服的官员们,制服虽然像地方警察,可是眼神却大相径庭,好像他们都是一帮没有见过老外的老外,见到老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行动异常,出人意料。他们都属于一个叫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单位,这个单位是在9·11以后把以前的移民局和海关合并在一块形成的。
在美国9·11以前的移民局臭名昭著,老美老外都不喜欢,民主党、共和党在为抬杠而抬杠的辩论中都能挑出这个机构的腐败、臃肿和官僚等等等等毛病。据说政客们如果被认命为移民局的领导,就相当于在政治上被逐放西伯利亚。
9·11以后这个移民局更逗了,给两个死去的9·11的劫机者发了两份迟到的学生签证,弄得美国人民一片怒骂。官僚到了如此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个机构被彻底地打散、重组,跟海关、边防合并,组成了新的部门。新的机构据说要运用更多的先进技术,与更多的政府部门联网、通讯,以便更有效地加强边防,防止恐怖主义者进入美国搞破坏。
柯不爽便是去上网查了半天电脑,没查出陈沓有恐怖分子嫌疑。但是这么便宜就让一个老外进入美国吧,不爽!于是在一张空表格上填上了陈沓有进入美国寻求非法工作机会的嫌疑,需出示更多的申辩材料以证明去美国是暂时的。
常言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要遇上一个核桃,这也没法说理。虽然提前三个半小时来到机场,看来今天是没法进入美国了,回家吧,一张机票四五百美元就那么浪费了。
一转身,这西北航空公司的服务还不错,竟然有西北航的服务人员进入了"研究研究谈话室",把一群今天被拒绝进入美国的乘客圈在一起,然后拿出大哥大对飞机旁的检票人员呼叫:"Victoria calling Marchelo,Victoria calling Marchelo,Looks like five will be stranded on this fight,Marchelo copy?"
"Copy"
"Go ahead and tack off! Over。"
西北航的服务人员耐心地跟大家解释,如何改签机票不至于浪费。
陈沓看着一圈被拒之于国门外的老外,抱以同情的微笑。他们看着像是老墨但绝非泥腿子,应属于有钱的一类老墨。其中一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像皇家马德里队的守门员,不,更应该说像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
还去美国吗?大凡生活就像是围城,城里的人拼命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去。今天冲不进去了,回家吧,能多跟老婆孩子待一天也不错。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风一吹,陈沓的脑子里老想着一首歌,这种现象叫Music worm。
The wind of change,
Continue blowing,
Every time I t-w-ried (tried) to stay。
The wind of change,
Continue blowing,
They just carried me away。
回到家,陈沓一五一十地告诉自己的老婆,一个正常的人如何变成一个狂人,而且要日记;如何在机场的海关边防遇上了一个核桃。这核桃在印象派的表现手法里面如何变得越来越像一个Girl,以致最后自己脑海里充满了那首"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的歌曲。
恒玉安慰道:"我们的陈文沓天生就是一个情种,有什么办法呢?"
陈沓申辩道,这世上只听说过一首叫《天生不是情种》的歌。要说到情种的话,自己的同事Michael Mayer才是一个情种。
陈沓在一家化学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叫Michael Meyer,上级来检查工作了,实验室里除了搞大扫除以外,还把每一个工作人员的照片贴在橱窗里,在每张照片底下写个名字再开个玩笑。Michael Meyer的照片底下写着:"I am not a chemist,I am a lover。"这是同事们对他的评论。他自己对自己的评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他的电脑上屏幕保护程序启动了,上面打着他自己给自己戴的好几顶高帽子:Sex God,Mind Jedi。
在把情种的玩笑开完了以后,陈家小两口严肃地商量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恒玉说:"以后你进不了美国了,咱们家可怎么办啊?美国这条路你一定得走通,再去试一次吧?记住你的事业在美国,你要进不了美国的话,咱们家可就揭不开锅了。"
为了进美国,陈沓只好求贵人相助。凡是提到移民的事,这贵人其实有时候也不怎么贵。比如一个移民要申请驾照延期,到人事部的前台找个小年轻写个介绍信也就行了,但手续是不能缺的。这一次既然那位边防官员柯不爽,要一些并非永久在美国工作的资料,那就叫合作伙伴朋朋写那么一封介绍信吧。
一个电话打过去,朋朋惊讶地说:"啊?你还没绿卡呀?有没有听说过common law marriage?你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以为你早就Common law green card了。"common law marriage就是生米煮成熟饭,煮得久了,想赖法庭也不让你赖掉赡养费的那种婚姻。
陈沓苦笑着给朋朋解释:"美国政府不发common law green card。"
朋朋又想了一个损招:"哎呀,当年你那么喜欢听Rush Limbaugh的Talk Show,你给爽两把打几个电话,他那么好大喜功,又那么有影响的人,说不定就资助你拿到绿卡了呢。"
"Hey,Rush,First time long time,I was die-hard communist,after listening your show,I am a die-hard ‘ditto head’ now。"
陈沓说:"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就一封短短的信,我给你写好了传真过去,你签了字再给我传真回来,好吧?明天见. . .哦对了,记住,一定要打印在有公司商标的信签纸上,然后再传真给我,好吧?谢谢啦!"
第二天,陈沓怀揣介绍信,再次去过边防,奇怪的是,这一次竟然没有被送进"研究研究谈话室",就顺利地进入美国了。想起了《阿甘正传》里那句名言:
"Mama said: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
|
|
| Home |
|
(c) 2006-2016 Best-fit T Be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