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移民监”里的另一个囚徒,陈沓开始盘算自己如何胜利大逃亡的脱困计划。
悲情所在的地方往往是那艺术和文学洋洋洒洒、血流如注、泪如泉涌之处,什么伤痕文学、上山下乡知青文学,都比不上囚徒文学宏伟壮观。
从中国的监狱里飘出来过千古绝句:
“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欧洲,就算那知名度评不上五星级的小小监狱里,也曾飘出过美丽的文字: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也是七步。于是盖世太保 冯 ·迪特利施上校说:“老实交待!你写的七步七步的跟曹植的七步诗是什么关系?”囚徒回答道:“267号牢房在歌唱,我的一生都在歌唱。
( 他既没有乐感,也没有嗓子,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执著于唱歌。 )”
描写监狱的电影的旁白这样说:“那天,大家都不知道Andy为什么要跑到典狱长的办公室里忘情的放意大利歌剧的唱片,还开大了高音喇叭。监狱绝大多数人没读过什么书,我们也听不懂歌里边唱的是什么,可是我们都成了歌剧迷。”
监狱有各种各样的,在一个国家州、省、地、市、县建立的监狱被称为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的统编教材里把它归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之一种;另一种规模更大的监狱是一个民族囚禁另一个民族,或把他们流放。比如巴比伦人流放以色列人,欧美殖民者抓捕非洲奴隶,德国纳粹洗劫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样的例子想来真是举不胜举。
西方的宗教、政治、历史、文学,都受其影响的《圣经》,前半部分《旧约全书》绝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描述着一个摩西领着被压迫的以色列囚徒出埃及的故事,由于可兰经和圣经前半部分讲的大多数是相同的故事,所以《出埃及记》在可兰经里也有描述。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监狱规模可以造得越来越大,于是好几个国家可以联合在一起压迫另外好几个国家,好几个民族可以联合在一起压迫另外好几个民族。
“嗒啦!”移民监落成了,可以开始剪彩开工使用了!今天的移民监究竟是谁压迫谁的工具呢?谁是压迫者,谁又是受压迫者,这个监狱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苏联红军步步逼近德意志帝国边境,1944年11月8日凌晨,5个人飞越前线阵地,进入德国占领区波兰,预定的降落目标是靠近德国边境的威斯基德山角,5个人中只有2个人知道这次行动计划的秘密。这次行动计划的秘密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故事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同盟国和协约国不分胜负,僵持不下,突然许多士兵听见战场上有人喊了一嗓子:“社员同志们收工咧!”于是许多士兵开始开拔回家,另外许多士兵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中士以及某些不认输的德国士兵们不断地对别的士兵说:“这是场外观众吹的哨子,比赛没有结束,没有结束!”混乱中又有人喊了一嗓子:“社员同志们开会咧!”于是一大帮外交官来到法国这个叫Versailles的地方,开他们的社员大会,签订了他们的《凡尔赛和约》,这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真的结束??!
《凡尔赛和约》中绝大多数的条文跟移民监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计算战争损失的条款却相当有趣,尤其是计算各国士兵的生命价值的公式是移民监形成的理论根据。这个公式大致是这样的: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一个英国兵不死,在他一生中他将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于一个健康的法国士兵在一生中将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于1.234个健康的德国士兵在一生中将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于0.678个健康的美国士兵在一生中将创造的价值;大致相当于3到4个幸存的俄国士兵在一生中将创造的价值……在凡尔赛的数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他们是这样想的,觉得很有道理,也是这样做的,说:拿钱吧!
长夜难明赤县天。在黑暗的旧中国,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想叫那帝国主义的算命先生算一算:一条中国人的命值几分之几条外国人的命?那帝国主义的臭老九们还不乐意,把人一推,把门一关:“出去出去出去,乡巴佬懂什么?我们在谈正事。”“啪!”那关门者关好门以后转过头来对同伴说:“野蛮人,没文化,还真以为自己是战胜国呢!”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计算人生命价值的公式,穷国和富国同一职业的人,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吧:同样在厨房里做大师傅,红案上切肥肉,白案上做馒头,很有可能在发达国家里做出来的一个馒头,拿到不发达国家去就被称作是20个馒头,而很有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里做出来的一个馒头,拿到发达国家去便被称作20分之一个馒头。不平等啊,不平等!剥削啊,剥削!
于是在二十世纪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中,人们不断听见“斗争”这个词,而斗争往往跟阶级联系在一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人民日报社论员文章: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家开出球籍'。”
在世界范围内也经常听见阶级斗争的战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可这真理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国民的平均生产总值,陈沓暗暗琢磨了一下,发达国家的工人兄弟干一小时的活,比我们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兄弟干两天同样的活赚钱还多,这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岂不是比我们不发达国家的小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若真有那么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那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是帮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帮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呢?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真理确实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所有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看来跟有效和实际的追求平等和反剥削的办法是跨过移民监的这堵墙,指望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给资本家掘墓是指望不上了,但是跨过这堵墙以后,做的馒头别人不仔细看也就以为是一个馒头顶二十个馒头的那种高尚馒头了。
自从陈沓留学美国和移民加拿大以后,绝大多数时间日常生活中做的馒头都被人们误认为是高尚馒头,可是每当跨边境过海关的时候,那边防哨卡的士兵同志们总是要盘查清楚,无论他学历多高,技术职称什么样,也无论在厨房里摸爬滚打了多少年的手艺,只要一看见他手里拿着中国护照,就是不让他轻易越过移民监的墙到发达国家去做馒头。
在飞机上跟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来的乘客聊聊天,大家同唱一首歌那就是谭咏麟的那首《迟来的春天》:
“面对的彷佛多么渺茫
更加上这道墙
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
怪不得发展中国家朋友提倡南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改善东西关系,这移民监的墙就存在在南北和东西之间。从这些穷哥们国家来的移民们凑在一起合计合计,发觉:美国的边境是最难过的,其次是英国的边境。
这不,一帮厨房的大师傅要到瑞典去出差,公司给买了大英帝国航空公司的机票,那拿着卢森堡、比利时护照的小伙子“噌噌”就过去了;那拿了加拿大护照的亚洲人和东欧人也就“嘎嗒嗒嘎嗒嗒”的过去了;拿着中国护照的陈沓和拿着俄国护照的Alex Volnov被拦了下来。陈沓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人员,平常号称信奉“顾客总是对的,顾客就是上帝”,可是只要一提到移民问题,马上像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一脸正气,露出了护法金刚的法律威严,要在文革里,很有可能跟他们的配偶划清界限。
为了让他们轻松活泼一点,陈沓说:“你们不都是加拿大人吗?何必把英国的国门看得那么紧呢?我知道你们名义上都还是女王陛下的臣民,可是你们有谁把女王供在家里天天拜呢?如果你们害怕我跟这位俄国同志是恐怖主义者的话,我们申请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时候你们不已经查过我们的历史背景一次了吗?给女王她老人家打个小报告不就结了?”
这严肃的大英帝国航空公司的加拿大雇员,不仅是法律学得好,而且还是中央精神吃得透的那一种。他语重心长的解释道:“你瞧瞧这个名单上的国家。据统计数字说,这些国家因为生产力比较高,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如果到了发达国家,概率上说他们不至于赖在那些所到的国家,所以持这些国家护照的公民是可以免签证进入英国的,或者到英国办理落地签证。中国和俄国不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我不能把你们放进英国。”
“可是我们不要去英国,我们只是飞过你们的希思罗国际机场,我们都不出去,我们是要去瑞典,预定的降落目标是靠近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国际机场。我们只不过是到瑞典去做几个馒头,不,编几天程序,溜达溜达就回来,不然也没事干啊在那儿,谁都不认识。”
“不行,拿着你们的护照你们是没法进英国,你们也没法飞过英国,飞过英国你们都得办过境护照。”
陈沓只好跟他的伙计Alex说:“波涛同志啊,看来我们共产主义者以前把反动势力分为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以种族来歧视人的叫种族主义者,那么以护照来歧视人的叫什么呢?叫他们护照主义者?还是叫他们公民权主义者?”
Alex波涛同志比较实际,认为还是应该试试用去瑞典的因公签证,看看能去欧洲别的什么国家,能从别的什么国家迂回飞过。
这以后他们才发觉,绝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是承认到瑞典去的因公签证的。不仅让持有者过境,而且还让持有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遛出机场看看附近的名胜,只不过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要凌驾于别的欧盟国家之上,再加一道锁。
久而久之,陈沓总结出一条规律:越是YES说的YEAH的国家,越喜欢叶公好龙。许多德语系的欧洲国家,说YES是“呀”,这就够叶公的了。要等到一个国家把YES说成YES,或者YEAH,那就更是雕梁画栋、地毯窗饰全都是龙。可是当龙王爷、龙国正、小龙女、龙的传人真的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叶公哪儿受得了这个呀?
随着对西方文化不断深入的了解,陈沓终于意识到:原来西方自由和平等的卫士多半是一些幽默作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捍卫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最有影响的人物邱吉尔爵士,就是那么一位幽默作家,Winston Churchill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诺贝尔提名委员会的心目中,他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和平的贡献还不如吉米·卡特、达赖喇嘛或者. . . 或者亚瑟·阿拉法特的贡献大. 后几位得的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况且邱吉尔爵士年轻的时候做过记者,可见邱吉尔爵士一直是位了不起的作家。
要说到幽默,邱吉尔先生一生如此。年轻的时候竞选国会成员,有一天邱吉尔先生对一位选民说:
“Can I count on your support? ”
“Vote for you? I'd rather vote for the devil.”
“But if that chap is not running。Can I still count on your vote?”
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投我一票吧。”
选民说:“投你一票,我还不如投给魔鬼呢。”
邱吉尔先生说:“可是魔鬼没资格参选,你还是把票投给我吧。好好的选票浪费了何必呢?”
正面教材里说到邱吉尔首相的时候,一般总是喜欢播放他的两段演讲:一段是邱吉尔首相鼓舞英伦三岛人民坚持跟纳粹斗争到底,如果他们能够坚持斗争到底的话。“If the empire live for a thousand years,when people look back,they'll still say: this, was our finest hour”;
另一段是他分析冷战开始的演讲:“An iron curtain has descended across the continent”
可是老邱不仅正式场合的演讲,日常生活中的俏皮话也是随手拈来。
有一个女人对邱吉尔开玩笑说:“Winston,If I were your wife,I'll put poison in your drink!”
“Nance,If I were your husband I'd drink it”。
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哎老邱啊,如果我是你老婆的话,我非在你酒里下毒不可。”
“小南,如果我是你老公的话,死得越早受的罪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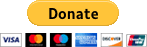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