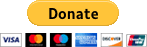| 中文 | 收听|Listen | English |
|
恒玉被自己丈夫的一番话说得不知所措,于是说:“唉,中国男足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怎么越说越来劲了呢?”
陈沓说:“那不是今天高兴嘛,拿了加拿大公民了,这就像农民工拿了城市户口一样。我不知道农民工换了城市户口是怎么庆祝的,我就多说话。”
恒玉突然想起一件事,说:“哎,以前你不说过,你拿到加拿大护照的时候,要在新的护照上把名字写成‘任我行’吗?”
“对呀,现在去好多国家都不用签证。‘多年以来,麦道飞机公司一直与中国西安飞机制造厂竭诚合作’,只要换一个护照,‘中国的航空事业也将随之而翱翔世界’。现在只是兜里缺几个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果兜里钞票鼓鼓的话我真是想到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我都不用叫‘任我行’了,我干脆改名叫‘任我玩’得了。”
恒玉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以后你到中国得签证了。不管怎么说吧,我的老公任我行或者我的老公任我玩都是好名字。”
“我要任你玩那得有钞票啊。说到弄钞票,到底到哪儿去弄比较好呢?还是去美国吧,好歹美国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要高一点。”
恒玉说:“你有信心和决心再在美国排七八年的队等绿卡吗?别忘了你是为什么来加拿大的。若是你再排七八年的队拿不到绿卡,然后又离开了,那可得做好进精神病院的准备啊。”
“咱们不是办绿卡过瘾嘛。没关系,再过七八年中国富强起来了,那时候再去申请一个中国的绿卡,也得等七八年,迎着困难上嘛。就跟我们那淮南来的日语老师说他自己一样,‘迎着困难上,共产党员嘛’。”
“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只猴子满山走,随你折腾去吧。不过我们身边这些拿了护照的朋友,真是将近一半的人已经回中国了,当然也有不少人去美国了。”
“现在而今眼目下,你叫我选的话,我觉得我的事业在美国,这也是我大哥当年给我做的选择。”
恒玉说:“又是你那个雷大哥,乔石抓人也不抓你呀。”
陈沓在中国科大念本科生的时候,同寝室的老大姓雷,名叫雷响,就是“春雷一声震天响”里边的“雷”和“响”两个字。
由于在七十年代末,中国北方的学校里边有春季改秋季招生这一说,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里,北方的孩子普遍比同年级的南方孩子大一岁左右。北方孩子成熟,显现领导才能,而北京孩子操着全国人民都能听得懂的口音,更是显得自信心四处洋溢。
雷响,乃北京孩子中的善之善者也,全班孩子都很佩服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也就是所谓北京“场面上”的话。
比如雷响有时在踢完球以后会邀请新认识的球友说:“哥几个凑在一块儿也不容易,来,到我们寝室坐坐?”另外有些时候会这么说:“哎,这位爷踢得不错,下周还来吧,我们每周四都在这儿踢,同一时间。”
就连雷响没精打彩的时候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也为同学津津乐道。
有一天,上《线性代数》的课,雷响迷迷糊糊就晕着了。台上一位操着广东口音的老师不知怎么谈到了:“年轻人要有理想(雷响)啊。”
雷响在半梦半醒之间以为老师提他问呢,于是晕晕忽忽就站起来了:“啊……林老师?”
林老师看见雷响站起来,觉得非常奇怪,但是不是他班主任,不知道他名字,于是说:“这位同学呀,你怎么站起来啦?”
雷响意识到自己要出洋相了,于是把带着睡意的语气慢慢变为平缓:“哦,林老师,您那x写的到底是三次方还是五次方啊?”
“是这个吗?这个?这是三次方啊。”
于是一个原本可以引起混乱的局面就这样化解了。
在雷响众多的语录中,获得全校知名度的是这一句:“乔石抓人也不抓你呀。”
那是六四以后,有一天在宿舍楼梯的拐道上,雷响和一帮好弟兄碰上一愁眉苦脸的同学,雷响开口问:“哎我说乔永军,干嘛呢,愁眉苦脸的?”
这位同学以为他自己在学潮里闹得太厉害了,于是神秘地说:“乔石要抓人啦!”
雷响顿了片刻,回过味来然后说:“嘿……瞧你丫的那奶奶样,怂人一个嘛,乔石他抓人也不抓你呀!”随后扬长而去。
雷响一边走一边给身边的陈沓说:“瞧见没?这就是我们的同学,一个个跟小土拨鼠差不多,可是偏吃那报纸广播电视上的迷魂药,夸他们什么大学生、天之娇子他们也就信了。那天之娇子是毛泽东、成吉思汗级的人物用的。‘后生,牛肉是给三炮留的,有你什么事啊?’”
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深情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陈沓的脑海里。每当有中外友人劝诫他应该在国外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做出不利于拿绿卡的事的时候,陈沓总是会想起雷大哥说的“乔石抓人也不抓你呀!”再加上“土拨鼠”三个字,于是觉得窝窝囊囊地做人图个啥呢?
当有人谈起中国人的体质、素质和气势,比吃肉和吃西餐的老外差的时候,陈沓便开始想念有血性的中国人。“夫专诸之刺王僚也,慧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还想到自己的古道热肠的像雷大哥一样的兄弟。
雷响语录中还说过:“你们怎么都那么看好令狐冲啊?我看他太拘礼于小师妹了,萧峰那样的燕云十八骑,千军万马吾往矣,那才是好男儿。”
这些故事陈沓告诉自己的妻子不止一遍。于是恒玉问他:“你现在跟雷响还有联系吗?”
“没什么实际的联系了,大家都围着老婆孩子转了,天若有情天亦老嘛,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我们回国探亲路过北京的话,我要不‘谷歌谷歌’,我可能还真联系不上他。”
恒玉微微的一笑,说:“用你的话说就是:又一个朋友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了。”
陈沓无可奈何的惋惜的摇摇头,回答说:“可是我时时刻刻都记着我大哥对我深情的嘱托,那就是‘我的事业在美国’。”
“你记得六四以后中国的大学里开始搞军训,因为觉得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八七年弄到八九年没什么效果,八九年秋天开学以后,干脆限制大学生出国,再每天放几首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歌。”
“有一天下午又要政治学习了,我午觉醒来以后,站在我们宿舍的窗子边,看见窗外水泥路上,我们年级的人一个个懒洋洋的要去开会。大会的主题是谈分配和限制出国的新政策,那时候时髦的提法是我的事业在中国。”
“为了给大家提提精神,我就跟着学校喇叭里‘接过雷锋的枪’那首歌,用合肥话给大家逗:
‘雷锋啥也别想,
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
雷锋啥也别想,
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隔壁寝室一同学看见我跟雷响了,于是就跑过来说:“嘿老大、老六,你们有没有那个烟屁股?”
雷响拿出一支烟来说:“我给你一根烟得了。”
我提醒雷响说:“人家找个烟屁股,是因为裤子上出了线头,想把它烫掉,政治学习的时候他想相亲去。你呢?给人一根烟,这不破坏他形象、坏他好事吗?”
那同学说:“哎老六说得对,是那么回事。”
雷响纠正他说:“什么老六?叫六爷!”
“哎六爷说得对,六爷说得对!”
雷响到烟灰缸里拿了个烟屁股点着了,死灰复燃以后打发了这位同学。
等他走了以后,雷响对我说:“老六啊,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如此地细致入微,如果毕业分配以后你在中国,你会不会感到无聊啊?我的事业在中国,是对我这种人说的,因为我不是六种人。你瞧瞧你,不缺胳膊断腿也不缺心眼,又是六种人,干嘛不到国外去看一看?要依我说呀,你的事业在美国!你要学着接过雷锋的枪,那你辈份就小了。你要学着到国外去找一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你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徒弟了,辈份一下就高了。”
陈沓接着说:“我出国以后一直没有忘记我大哥对我说过的这一席话。”
恒玉惊诧地笑了:“嘿嘿,从我们认识、谈恋爱、结婚,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有那么大的志向在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呀?”
陈沓见自己的妻子误会了,于是便耐心地解释说:“我不是在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那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早就有,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不用到国外去找,那GDP照样发展起来。你看那老外不管学什么都吭哧吭哧的念《孙子兵法》:‘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说的不就是越战和伊拉克战争吗?再说那救国救民的真理哪儿是我找的?‘乔石抓人也不抓你呀!’”
“雷大哥叫我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话我是当耳旁风,我所牢记的是他另一部分教导。这么多年来生活在国外,我苦苦的探索和寻找的,是那西方文化里面神秘的烟屁股。常言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咱们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好像英语听懂了,但是这话中的话,音里边的音,到底有没有听懂呢?”
恒玉说:“听去吧,听去吧,找去吧,找去吧。I being searching for something,something so undefined. It can only be seen, by the eyes of the bli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陈沓说:“她说英语了,她说英语了……”
这原是周润发演的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不过现在在海外的许多中国家庭里父母经常用这句话来督促孩子学中文。
在一旁玩耍的冰心听见父母说这话便紧张,于是她转过头来,老大不情愿地说:“你们又要我学中文啊?”
陈沓觉得今天可以对女儿要求松一点,就对她说:“啊对,你得学。不过你今天可以从DVD上学吧。你要看《猴哥》,还是《还珠格格》,还是《纪晓岚》?
女儿选了《还珠格格》,到一边去钻研她的满族人说的中文去了。
陈沓接着跟他的妻子讨论小学生学文化的问题:“我总觉得吧,我们这帮人出一趟国拿几个学位,然后就回中国招摇撞骗的话,那英语的文化程度就跟这帮不争气的ABC的中文的文化程度一样,我真会害怕那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比如我那雷大哥要见到我,问我在美国一个烟屁股到底有什么用途,我肯定答不上来。他出题再简单一点,说‘你到美国念那么多年书,混了那么多年,总不能做个没文化的人吧?来,你告诉我,谁是西方有名的书法家?谁是说英语的有名的诗人?像那些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一样,在美国每个小孩都能背的儿歌你能背几首?’”
“虽然这些对于我们学理科的人来说都是装点门面的知识,但在中国你要做个大学生,不知道谁是李白、杜甫、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那有文化的人不笑话你才怪呢。考题再简单一点,我在美国接受了那么多年高等以上教育,但是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很轻松地用英语说出‘胆囊炎、胰腺炎、肺气肿、色素沉淀’,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这可是常识性的问题呀,我连这都不会,那就不好意思对父老乡亲们说我学成归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到美国去寻找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和神秘的烟屁股。”
恒玉用小时候从相声里面学到的一句话潮笑自己的丈夫说:“去吧去吧,去开吧,去啃吧,去啃你的处女地吧。”
停了一会回过神来她又说:“哎,好像西方人对书法家和诗人没有那么尊敬,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那么多领导人和乾隆皇帝爱写诗爱留字画,这儿的名人时兴扎上一根红头绳或者男的梳他个爆炸式的公鸡头,追星的就一大帮一大帮的来了。”
陈沓笑了说:“嘿嘿,没文化了不是?咱们若有机会游遍西方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西方的艺术家要都不签名、不题字、不自我炫耀,那我把头剁了给你。我们在英语里面对这些文化人的了解还达不到一个装饰性水平,那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读万卷书也没机会行万里路啊。”
“这几十年来东方和西方搞得跟个你在唐朝我在汉似的。弄个签证吧,‘啪’,一指那老头,‘他不……给……办(京剧腔)’,这样的环境谁还学谁的文化?你还说什么追星呢。追星,那是刚从乡下搬到城市里,接受了高小文化教育的人干的,你现在看着那一个个星,还有那城里人那水灵劲儿嘛。好好再提高几年英语环境下的文化水平吧我的同志,这样我们就不会说‘English level’英语水平‘No Three No Four’不三不四,’We’ll deliver your luguage to four sides and eight directions’ 我们将把你的行李送到四面八方。”
恒玉接过学英语的话题说:“嘿,这英语真是难哪,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到那么多年英语,以为自己英语不错。后来想一想,当年我们那外教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密苏里来的乡下人,我们同学还笑,说洋人怎么会是乡下人呢?现在转了那么十几年,想一想,他可能当时教我们的英语真的是乡村女教师教的英语。”
陈沓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外教,他是亚历桑那州来的,你现在在北美提起亚历桑那,就跟在中国提起贵州一样,地处西南边陲,不仅想起的是乡下,还想起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过咱们还是应该尊师重教,讲点良心,不能责怪那老外把我们的文化水平压得太低了,他当时如果教深了我们也听不懂。我记得他当时讲英语里面的一词多义:Break这个单词,可以作‘刹车’,也可以作‘休息’来解释。完了,没了。如果他真想教我们深一层的美国城市里面劳动人民的hip-pop的文化的话就该说:
‘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if you got what it takes
‘cause I’m Kurtis Blow, I want you to know
these are the breaks
. . .
Breaks on the bus, breaks on the car
Breaks to make you a superstar
Breaks to win and breaks to lose
These here breaks will rock your shoes
well, these are the breaks . . .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If your women steps out with another man,
that’s the “break”, that’s the “break”
She runs out with him to Japan
that’s the “break”, that’s the “break”
IRS says they want to chat
you can’t explain why you claimed your cat
that’s the “break”, that’s the “break”
Ma Bell sends you a whopping bill,
with eighteen phone calls to Brazil
that’s the “break”, that’s the “break”
and you borrow money from the mob
yesterday you lost your jobs
well, these are the breaks . . .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break it up
瞧这首歌里面,break这个单词显出多强的多样性,而且这才是三段里面的一段呢。”
恒玉说:“英语这玩意,你要一直想学下去的话,学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永远也学不完。”
“哎呀,我也很烦恼啊,以前电视上告诉我们,学英语是为了面对将来的国际竞争,迎接挑战,算是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吧,可没人告诉我们,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在这种竞争中不殆呢?后来看见欧洲人、美洲人、亚洲人都说英语,简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咱们也就随大遛了。反正嘛人的一生就是应该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一生已经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那就是追求人类的平等,缩小城乡差别、东西差别、南北差别。”
“那说英语的人耍了一小时笔杆子能挣多少钱,我就希望耍一小时的笔杆子能挣多少钱;那会说英语的人编了一小时程序挣了多少钱,我编一小时程序也希望挣那么多钱;那会说英语的人做了一小时馒头挣了多少钱,我做了一小时馒头也希望挣相同的钱……”
恒玉打断丈夫的话说:“你们贵阳人那么喜欢吃馒头吗?我一直以为北方人才在乎做一小时的馒头挣多少钱。”
“嗯……其实馒头这个东西呀,源于中国西南地区。传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降服孟获以后,班师回成都的路上,无法再次渡过泸水,因为泸水之上风雨大作,藤甲兵的鬼魂叫屈喊冤。诸葛丞相想平息老天爷的愤怒,又舍不得砍掉士兵或者牲口的脑袋祭天,于是就用白面做成了头的形状作为祭品。直到今天,你如果把‘面’和‘头’两个字用成都话或者云南话发音,那就是面头(馒头),这就是馒头的由来。后来被北方人剽窃了,全国人民大多数以为是他们的作品。”
恒玉说:“瞧你,夜郎自大的毛病又犯了。好吧,就算世界上第一个馒头产于你们那片区。人家问你伦敦看着怎么样,你说看着‘像贵阳’;有朋友问你斯德哥尔摩看着怎么样,你说‘哎呀欧式建筑就是美呀!发诺贝尔奖那大楼啊,看着就跟文革时期的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号病房差不多’这都什么呀?”
陈沓辩白说:“我后来多去那些城市几趟以后,不也承认了吗?那些作为首都的城市,人家有皇宫,那里边国王刮来的民脂民膏还是比我们贵州省政府苛捐杂税来得东西多得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夜郎文化作为其中一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西方津津乐道的耶酥受难的故事前后不久,我们就有了夜郎自大的故事。后来我离开了贵州,上大学的时候我当着全国各地来的同学,我想给他们做做贵州的广告啊。那时候老干妈还不太出名,所以我只好夸夸我们贵阳的王二公。我用那瑞士雷达表的广告的语气说:
贵阳,人杰地灵,科技优秀,
贵阳王二公,把优美的工艺和现代化科技融为一体,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方言剧。
贵阳王二公,创崭新时尚,与时间并存!
每次我一提到贵阳科技优秀,我们那些同学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连我贵阳来的同乡都告诉我:咱们贵州是中国的第三世界,中国在国际上是第三世界,所以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说,贵州就是第九世界……嘿,我觉得我这同乡乘法学得不错,说得在理。
贵州各族人民跟全国各族人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乘法按比例放大的关系。西南边远地区,夜郎自大了那么一下,落后了吧?中国,几百年前夜郎自大了一下,现在也在国际上落后了好几十年。
这五十年代吧,周恩来总理去贵阳游玩了一趟花溪公园,挥笔题字:贵州山川秀丽、人民勤劳,假以时日,必定后来居上。
在我长大的年月里,就有乡亲拿着这句话当法宝,证明贵州以后一定会后来居上。可是到外地一打听,周总理?听说过;花溪公园?有的听说过;这个题词?基本上就没人听说过,贵州的前途嘛……那个外地人说:唉咱们不讨论这个好不好?哦对了,中央在开发西部。
你把这种现象放大几倍的话。几百年前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等他醒来的时候会惊动世界。
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经常有人喜欢用这句话来证明中国必将强大起来。把这句话拿到外国一问,拿破仑?听说过;睡着的狮子嘛?唉呀,拿破仑一生比喻太多了。他说如果让教皇给他加冕的话,他得把教皇的手捆起来然后才能吻教皇的靴子。别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他就说,法国的王冠掉在地上,我只不过用宝剑把它给挑起来了,歪戴帽邪穿衣的往我头上一扣,正合适。就这么一位老说俏皮话的主,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段“看得过去、听得顺耳”的谎言,那么他的预测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自强自强,还用得着引用老外给自己打气吗?
跟老外谈到中国要惊动世界那一部分,那老外有几种反应。
一种反应是说:“唉,咱不谈这个。啊你好久没回家乡了吧?你们那儿是不是开了很多厂啊?我们这儿关了好多厂。”
老外的另一种反应,就像那个自称 Cokie (Roberts) 的电台兼电视台女播音员评论江主席的一段话:江泽民同志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想向美国人民伸出友好的橄榄枝,于是他说了类似以下的话“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可以互相学习……”后来 Cokie在电视上评论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搅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我们从这么一个共产主义的、不讲人权的、不讲民主的中国,能够学到什么?”
听着这种评论,我就想起我们贵州人民一直背着的一个千古奇冤。作为贵州人到外面混吧,顺利的时候还行,不顺利的时候啊,迟早会有人说你黔驴技穷,好像我们贵州老产驴似的。可是你要翻开古文看一看,他原文是那么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那贵州的驴都是外面运进来的。
后来长大了我发觉,你要在西方发达国家混吧,跟老外合作愉快的时候还可以,若是有竞争,或者竞争太激烈的时候,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公司与公司之间,那从中国来的部分总会被人嘀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个不讲民主的、没有人权的国家耍小花招的干活……”
可是中国本没有共产主义呀,他就像黔驴一样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啊,船里面还包括着兵舰,中国人不要吧,那船上还开炮呢。
那西方出产的共产主义拿到中国,反围剿吧,教条主义了;肃反吧,扩大了;反右吧,冤假错案了;搞经济建设吧,冒进了。
共产主义真正有两下子,那是在中国的有识之士把它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后,才威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呢,这么阴差阳错的,弄得好像中国人比什么国家都共产主义了。
有的时候吧,我真想对西方人民说一句:你害怕共产主义吧,不用害怕中国的游客;你害怕中国的流浪汉吧,就跟害怕你本国的流浪汉差不多,都是人嘛,同样对待就行了。”
沉默了一会,恒玉说:“可是谁叫你这么热爱流浪的生活呢?年轻的时候吧读三毛写的东西,她说:流浪的生活是浪漫的。年老了以后吧,不,年纪大一点以后吧再回味她写的东西,她也说过:可是流浪的生活是无奈的和辛苦的。”
“三毛, 对了. 三毛就是她.” 陈沓说: “流浪的生活也是滑稽的,荒诞的和有趣的. 我想出外流浪的思想根子, 就是她盘下来的. 文革刚过的时候我唸初一. 四人帮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 那时候我们班主任老师批评同学批得兴起,立刻就会说:我要到你们家贴大字报. 我要在你们家驻的那条街上把你搞倒,搞臭! 那时候我们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还穿着解放绿或者人民蓝.可是有一个教音乐的女老师穿的蓝好象有点儿海军的蓝,或者是红军的灰。反正跟人不一样,然后头发上还烫着象绵羊一样的卷儿。这天上音乐课她教了我们两首特别奇怪的歌。
第一首是统编教材里的一首苏联歌。这首歌不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但是课本儿里写着: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特别喜欢这首歌。
感受不自由
莫大的痛苦
你毅然地抛弃了生命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英勇, 你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英勇, 你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倪勇,倪勇, 你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倪勇,倪勇,倪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倪勇,倪勇,倪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 . .
停!
. . .
倪勇,倪勇,倪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 . .
停下来,停下来。
. . .
倪勇,倪勇,倪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 . .
停了,停了,停了。叫你们停没听见吗?最后几句话重复三遍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次。
可这位音乐老师永远也想不到。班上有一位叫‘倪勇’的同学。所以这班上的三十二个男孩儿和三十三个女孩儿都觉得唱着他们的同学人头落地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接下来那老师用手一指黑板儿说:这首歌课本儿上没有。我把它写在黑板儿上了。你们先读一下。然后我先唱一遍。你们再跟我学。
同学们一看黑板上那首歌,好多人心里就嘀咕:嘘,这个。 。 。 这歌词倒是按着中国语法写的。可是意义上比第一首歌更难理解。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为了山中轻流的小溪
为了林间飞翔的小鸟
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
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那橄榄树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为什么人为了橄榄树就做那么多疯狂的事儿呢?
” 


|
|
|
| Home |
|
(c) 2006-2016 Best-fit T Beta |